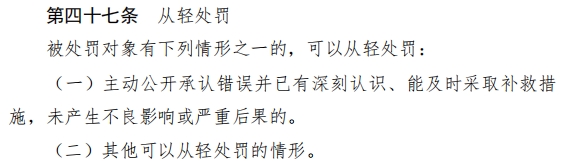“打脸裁判”事儿不小,对第46号处罚的理解与思考背景:“打脸”裁判的前国奥队长一场在六一儿童节当日进行的中乙联赛,却因为前97国奥队长姚道刚极不冷静的“打脸”裁判的行为而受到广泛关注。
2023年6月4日,中国足球协会官网公布了纪律委员会针对该事件做出的“2024年第46号处罚决定”,对姚道刚停赛12个月,并罚款人民币10万元。
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2024版,“纪律准则”)相关规范内容以及既往处罚实践,一份纪律处罚的形成通常包括确定违纪行为的构成与性质,确定违纪行为适用的规范,确定违纪行为适用的处罚情节等步骤,并最终形成处罚。本文将从上述三个层面对该份处罚进行解读,并与读者分享一些处罚之外的思考。
01 理解第46号处罚1.行为认定:
暴力行为从已经公布的“2024年第46号处罚”内容来看,姚道刚的违纪行为主要包括:
①推搡并辱骂裁判员;
②用手推击裁判员面部。
其中第46号处罚中明确将“后一行为”(用手推击裁判员面部)评价为“暴力行为”,而对“前一行为”(推搡并辱骂裁判员)仅在处罚决定中进行了描述,但未做明确评价。
参考足协既往处罚案例,从行为性质来看辱骂裁判员属于“纪律准则”第五十四条第(一)项明确的“非体育行为”,而“推搡”似乎同样可以认定为“暴力行为”。
但由于该处罚仅对“后一行为”的性质进行了认定,故该处罚实际将“后一行为”作为其处罚的基础,而“前一行为”仅作为确定处罚情节予以考量。
注解:“2023年第72号处罚”【韦世豪鼓掌案】、“2023年第115号处罚”【张稀哲骂裁判案】以及“2023年第144号处罚”【高准翼骂裁判案】,在上述处罚案件中纪律委员会均认定上述行为构成“非体育行为”,并依据“纪律准则”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作出处罚。
2.条款适用:第五十四条第(二)项根据该处罚内容显示,纪律委员会依据“纪律准则”第五十四条第(二)项对姚道刚进行处罚。
根据“纪律准则”第五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对比赛官员实施暴力行为的,至少停赛6个月罚款人民币10万元。
 3.处罚情节:从重处罚
3.处罚情节:从重处罚在认定姚道刚的行为属于暴力行为的情况下,同时考虑其推击部位为裁判员的面部,属于“纪律准则”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可以从重处罚”的情形(“侵犯部位系头部、面部、裆部等”),纪律委员会在适用罚则时对其从重处罚。
 4.处罚情节:非顶级联赛罚款减免
4.处罚情节:非顶级联赛罚款减免根据“纪律准则”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对于非中超中甲联赛中发生的违纪行为,纪律委员会可以酌情减轻对其罚款的金额。由于姚道刚的违纪行为发生在中乙联赛中,不属于中超、中甲联赛,故纪律委员会可以依据“纪律准则”第一百一十条对其减免罚款金额。

5.处罚情节:从轻处罚(未适用)
根据“纪律准则”第四十七条之规定,赛后主动承认错误、有深刻认识,采取补救措施的可以从轻处罚。
通常情况下在发生违纪事件后,违纪方的表态(承认错误,道歉等)属于可以从轻处罚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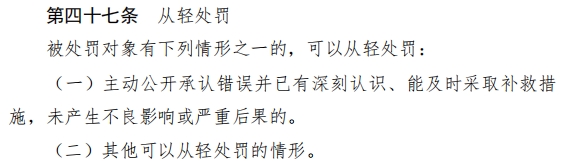
例如在“2024年第12号处罚”中,纪律委员会对廊坊荣耀之城球员魏超伦的事后主动承认错误的行为予以认定,并适用“纪律准则”第四十七条从轻处罚。

但从“2024年第43号处罚”来看,即使成都蓉城俱乐部赛后在其社交媒体上公布了关于违纪行为人杨帆向对方球员当面致歉的视频,但纪律委员会综合考虑仍未对其从轻处罚(同时适用从重处罚条款),这也符合“可以从轻”的规范内涵,即决定权在纪律委员会。

具体在本案中,尽管姚道刚及其所在俱乐部在事后均采取了补救措施(道歉及队内处罚),但最终纪律委员会未对其适用从轻处罚条款。
 6.处罚幅度参考:既往处罚案例
6.处罚幅度参考:既往处罚案例自2022年以来,纪律委员会做出的针对球员向比赛官员实施暴力行为,且同时存在“从重处罚”情节的处罚案例主要包括:“2022年第1号处罚”即杨浩宇案,“2022年第58号处罚”即恩里克·多拉多案。
在上述两案中,涉事球员均对裁判员实施了暴力行为,且存在“从重处罚”情节,纪律委员会均对涉事球员做出了“停赛12个月,罚款人民币20万元”的处罚。
综合上述行为定性、处罚条款以及处罚情节:
针对停赛场次,纪律委员会在基准处罚停赛6个月的基础上,考虑了从重处罚情节以及既往案例,对姚道刚做出了停赛12个月的处罚。
针对罚款数额,纪律委员会在基准处罚罚款人民币10万元的基础上,考虑了非顶级联赛减免条款、从重处罚情节以及既往案例,对姚道刚做出了罚款人民币10万元的处罚。
02 救济: 中国足球协会纠纷解决委员会根据《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第五条之规定,对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做出的符合《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的处罚,可以向中国足球协会纠纷解决委员会申请仲裁。
参考“纪律准则”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本处罚系针对自然人做出的停赛5个月以上的处罚,属于纪律处罚纠纷的仲裁受理的范围。
03 第五十四条: 对比赛官员的倾向性保护“纪律准则”针对相关主体实施不当行为的对象的不同,分别规定了第五十三条“对对手或其他人(除比赛官员)实施不当行为”与第五十四条“对比赛官员实施不当行为”。
即当不当行为的实施对象为“非比赛官员”时适用“第五十三条”,对象为“比赛官员(裁判)”时的适用“第五十四条”。
注解:“纪律准则”第六条明确比赛官员包括:裁判员、助理裁判员、第四官员、视频助理裁判员、比赛监督、裁判监督、安全官员,以及中国足球协会或会员协会指派的和比赛有关的其他任何人员。
从处罚幅度来看,“纪律准则”与我们比较熟悉的《刑法》或《治安管理处罚法》不同,具体违纪行为对应的罚则一般仅规定处罚下限(即至少给予停赛x场,罚款人民币x元),处罚的上限则在总则条款中予以确定。即通常在适用罚则时,违纪行为所对应的都是单一的处罚区间。
具体而言,“第五十三条”中规定有四类违纪行为,包括
1.严重犯规(处罚下限:停赛1场罚款1万元);
2.非体育行为(处罚下限:停赛2场罚款2万元);
3.暴力行为(处罚下限:停赛3场罚款3万元);
4.吐口水(处罚下限:停赛6场罚款6万元)。
其中规定的处罚幅度下限最高为“停赛6场罚款6万”。
“第五十四条”中规定有三类违纪行为,包括
1.非体育行为(处罚下限:停赛5场罚款5万元);
2.暴力行为(处罚下限:停赛6个月罚款10万元);
3.吐口水(处罚下限:停赛12个月罚款20万元)。
其中规定的处罚幅度下限最高为“停赛12个月罚款20万”。
因此,从“纪律准则”将针对“比赛官员”实施的不当行为单独列为独立的条款并处以较一般对象更为严重的处罚来看,“纪律准则”对于比赛官员的倾向性保护不言而喻。
04 思考: “暴力行为”与“非体育行为”的界限“纪律准则”第五十四条针对不当行为进行了三种列举和分类,除了第三类“吐口水”为具体行为外,第一类“非体育行为”与第二类“暴力行为”均为对行为的概括。从规范文义内容来看,对上述两类行为均采用了“不完全列举”的定义形式。
其中“非体育行为”行为包括“指责,使用具有攻击性、侮辱性或辱骂性的语言、手势或动作”。“暴力行为”包括“肘击、拳击、踢打”等。
从文义上看,“非体育行为”与“暴力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违纪行为人是否与比赛官员发生实质性接触。
但是需要思考的是,在上述两类行为之中,是否存在“中间地带”,例如“有接触但非暴力”的行为,这一类行为是否因为其与比赛官员产生接触就认定“暴力行为”?尤其是在考虑“非体育行为”与“暴力行为”的处罚基准差距较大(停赛5场/停赛6个月)的情况下。
一方面,按照一般理解在行为认定时,除明确与列举行为一致的行为外,被认定之行为应当与条款所列举的行为具有同质性。而被认定为“暴力行为”的行为必须与“肘击、拳击、踢打”具有同质性,显然从行为的危害性来看,一般的接触和“肘击、拳击、踢打”等暴力行为是有本质区别的。
但另一方面,如果从“立法”对比赛官员倾向性保护的立场出发,从严认定似乎也无可厚非。因为裁判员作为赛事规则的象征和代表,不容侵犯。同时,行为的同质性并不仅仅考察行为本身形式上的同质性,而应该结合场景判断实质的同质性。例如,用手指推击裁判员面部这一行为已经区别于一般的非体育行为,并且在对规范秩序的破坏意义上具有列举行为(“肘击、拳击、踢打”)具有实质上的同质性。
随着近年来中国足协对相关纪律处罚的公开力度的加大,规范的进一步细化,以及相关处罚的数量的不断增加,或将对上述行为的分类以及处罚的适用有更好的指引和完善。
本文作者
李辉煌(合伙人)
上海市律师协会体育专业委员会 委员
邮箱:lihuihuang@riyinglawfirm.com.cn
业务领域:争议解决、金融类法律服务、体育娱乐法律服务
李辉煌律师,于华东政法大学取得法律硕士学位,执业以来主要从事争议解决业务,尤其深耕证券金融、体育法领域。
在证券金融领域,李律师曾先后为包括但不限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大型国有金融机构提供诉讼与非诉讼法律服务。
在体育法领域,李律师曾先后为某中部中超俱乐部、某华南地区中超俱乐部提供非诉、诉讼、仲裁等法律服务。他曾代表客户出庭处理在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国际足联争议解决委员会(FIFADRC)以及国际体育仲裁院(CAS)的仲裁及上诉案件。